吉野彰成為日本19年來第19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更新時間:2023-10-29 16:12:16作者:佚名
10月9日,當地下午11:45(上海時間上午5:45),加拿大皇家科大學宣布日本 諾貝爾獎,將2019年諾貝爾物理獎授予英國科學家約翰·B·古迪納夫、英國物理家M·斯坦利·威廷漢、以及美國科學家吉野彰,以嘉獎她們在鋰離子電瓶方面的貢獻。
其中引人注意的是,吉野彰也以此成為了法國19年來的第19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成功保持了瑞典平均一年一位諾貝爾的記錄。
近些年來,美國在諾貝爾獎角逐中“大出風頭”,這一切須要溯源到19年前,美國政府的一項重要決策。
2001年,意大利政府提出了個“豪氣干云”的科技計劃——要在50年內拿30個諾貝爾獎。
不出所料,這個計劃被指責了,笑的人不是他人正是自己人,但是還是當初剛拿諾貝爾物理獎的野依良治。他毫不客氣地評價政府的這些計劃“很傻帽”,雖然之前的100年只出了9位德國諾獎得主。
接出來,就是喜聞樂見的“打臉劇情”了。
計劃執行了19年,獲諾獎的美國人已有19位。從結果來看,這個目標不但不傻,還非常保守了。
美國在科學界的成果這么亮眼,導致了他國的羨慕。尤其是鄰國中國,關于臺灣諾獎的文章不計其數,有倡議學習模仿英國的,也有反思批判本國教育制度的。
2008年諾貝爾化學學獎獲得者益川敏英
本以為臺灣的學界和媒體應當是對近些年的成績不說得意,也應當是滿意的,但當我查詢了大量報導以后,我倍感了焦慮。
臺灣的聲音主要并非總締結果,而是反思和居安思危。她們覺得,得獎的人多是年事已高的老研究者,她們手中的多是20年前的科研成果。而更多的學者談到了眼下學界人才寥寥、青年人不愿涉足科研的現況,推測接出來美國會步入“諾獎荒”,不少人倡議政府對學界松綁,鼓勵青年參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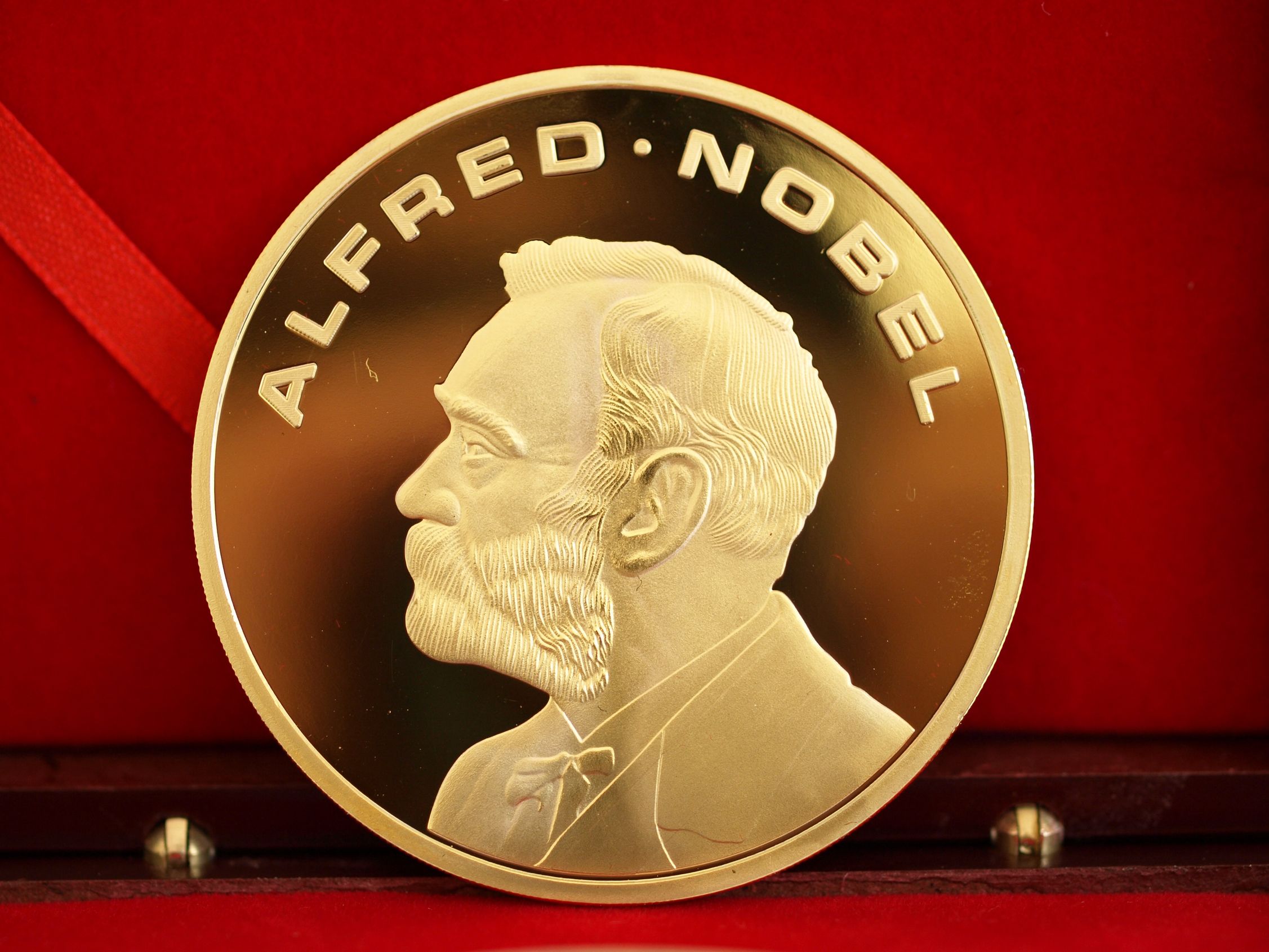
可道是,學霸學習好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不知足,還挑燈夜戰。
01
時間的檢驗
回顧臺灣近20年的諾獎成就,集中在數學、化學、“生理學或醫學”三大領域。統計出來,2000年之后的臺灣諾獎獲得者的得獎成果,大都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前后取得的,比她們獲諾獎時間要早二三六年。
拿去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京都學院院長本庶佑來說,他從上世紀70年代就開始研究免疫抗原,他的主要成果是1992年獲得的,從出成果到拿諾獎,等了26年。
201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本庶佑
這兒必須提及諾獎的評比特點之一——可靠性。科學常常是不斷推翻前人闡述的結果,牛頓推翻了傳統熱學,愛因斯坦推翻了牛頓熱學。某種程度上來說,科學飽含了后人對前人的“打臉”。
諾貝爾獎同樣不可防止地存在“打臉”。
1906年的物理獎發給莫瓦桑,緣由是他合成出了人造金鋼石,但后來發覺是助手搞出的烏龍騙子。1949年的生理學或醫學獎發給莫尼斯,緣由是他發覺了腦白質切斷術對個別精神疾患的醫治價值,但是這些具有嚴重副作用的療法后來被嚴禁了。
194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法國人莫尼斯
楊振寧和李政道在提出“宇稱不守恒”的第二年就獲諾獎,這屬于特例。研究成果是否可靠,須要時間的檢驗。在自然科學領域,這個時間多為20年以上。
本庶佑也坦承,科研之路是極其漫長的,尤其是基礎研究。他說,研究成果要回饋社會歷時較長,又常年得不到認可,這對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形成很大影響。他期盼社會更加寬容地對待基礎研究。
基礎研究苦,置于任何國家都是一樣。諾貝爾獎的籌建,正是拿來激勵這些把青春奉獻給科學事業、并為人類作出杰出貢獻的科學家們。
02
錢是萬X之源
回歸到為什么美國能在這20年就像“井噴”式地產出諾獎,就要追溯到幾六年前。
科技發展與經濟發展脫不開關系,你很難看到一個窮國長出醒目的科技樹。臺灣戰后經濟年均10%的高速發展,給科技發展提供了堅強后盾。
1960年,美國在制定“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同時,還制訂了與此目標相呼應的“振興科學技術的綜合基本新政”,提出要力爭將國民收入的2%用于科研。充裕的資金吸引了優秀人才,也帶來了先進的實驗儀器與富足的科研經費。
1960年代的美國商鋪
到了70年代,出口經濟蒸蒸日上的美國,漸漸打響了MadeinJapan的幌子。憑著物美價廉的產品,日貨為本國帶來了巨大的利潤。政府進一步增強了科研總額比列,目標將國民收入的3%用于科研。到了1975年,法國的研制經費早已超過了法、英兩國的研制經費之和,即將進入科技大國的行列。
教育變革是美國科技騰飛的另一關鍵誘因。來到明天的臺灣,你會發覺一件非常的事:別看美國國土面積小,而且學院愈發的多。國立和私立自何必說,公立學院多如牛毛。不同于普通人對學院校園的印象,有些公立學院并無校園,只有一棟樓作為教學場所。
1963年,中央教育審查大會向文部省提出了題為“關于改善學院教育”的咨詢報告。報告里提出的例如擴大教育規模、增設理科類的高等教育機構等建議,對后來的法國學院教育形成了深遠影響。
東京學院
其結果突出表現在,1960年至1970年間,美國高等教育機構的總量從525所降低到921所,降低了75%。
中學增多了,學院生自然也多了。臺灣并非僧多粥少,而是僧少粥多,有些學院都招不到人,為生源而苦惱。70年代的學院生比前六年多出了2.4倍,學院活脫脫一副“全民教育”的樣子。
更多的青年人步入學院,自然也就有更多的人涉足科研。科研成果的最佳證明是哪些?自然是論文數目。
按照美聯社的報導,1982年英國在五個科學領域發表的論文數目為12534篇,僅次于發表數目為33744篇的日本,位列世界第二。
再仔細觀察下,你可以發覺,臺灣的諾獎獲得者多集中于東京學院、京都學院、名古屋學院等國立綜合學院。這幾所學院都為戰前的“帝國學院”(七帝大:東京帝國學院、京都帝國學院、東北帝國學院、九州帝國學院、北海道帝國學院、大阪帝國學院、名古屋帝國學院)。
京都學院
戰時淪為各種裝備制造場所的帝國學院,在戰后被改建為以研究為主的國立綜合學院。不少國立學院都崇尚校風自由、研究至上的觀念。
這從側面說明一件事,不僅“全民教育”潮流提高民眾整體素質,更優秀的臺灣國立學院的科研環境與生源質量,是可以培養出諾獎得主的。

臺灣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以后,研制經費投入不斷減小,這為科技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而學院擴大教育規模、調整學科結構與青年中學生的增多等誘因綜合上去,為臺灣諾獎的產出創造了得天獨厚的環境。
03
諾獎危機
但是,經濟泡沫破滅后的臺灣,遭受了幾六年經濟停滯之苦,這一點也反射到了科研中。
美國政府每年還會發布《科學技術藍皮書》,總結臺灣的科研實力和存在的問題,并與全球主要國家進行比較。
今年的藍皮書強調,在世界主要科研大國中,只有英國研究人員發表的論文數目減小。全世界引用次數排行前10%的高質量論文中,美國占比從世界第4位降至第9位。而在政府科研預算方面,臺灣2018年的投入只是2000年的1.15倍,屬于一個幾乎停滯的狀態。似乎占比仍較高,但從增量上來看,在世界主要科研大國中最少。
不容豁達的現實,并非只顯示在數據中,綜合筆者在日留學的經歷也能綜觀一二。美國學院生的首選,都是提前步入社會,最優秀的人會被最好的公司盜走。而留學深造或讀通讀博,是她們特別靠后的選擇,一方面是由于科研苦,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待遇差。
大隅良典院士曾多次抒發對年青研究人員的期望
在臺灣的研究生群體中,超過一半的中學生都是中國人,另外20%是其他國家的人,美國本土研究生不足三成。青年人遠離科研,是美國高等教育的現況。
一方面是諾獎領到手軟,另一方面是科研環境的每況日下。好消息與壞環境并存,一定程度掩藏了問題本質不說,政府形成錯判,錯過變革的良機,才是惡事。
今年,臺灣的多本刊物都出了諾獎專刊,其中在《東洋經濟周刊》中,諾獎獲得者梶田隆章就毫不指摘地給學界叩響警鐘:研究資金、研究時間和研究人員數目,是決定論文數目的三大要素,倘若英國在這三個方面繼續惡化,未來將無法獲得諾獎。
另一位諾獎獲得者中村修二,則站在更高角度批判了整個歐洲的教育制度。他覺得,美國的學院入學考試制度十分糟糕,中國和日本皆這般,教育的惟一目標是考入知名學院。歐洲的教育制度浪費了太多的青春和生命,應當因材施教,讓年青人學習不同的東西,而不是為了應付考試而學習。
2014年諾貝爾化學學獎獲得者中村修二
中村修二的故事愈發催淚,他出身于普通漁船家庭,考試能力也平平,只考入臺灣三流學院德島學院。德島學院沒有數學系,但他對化學學具有深刻的理解,完全靠自學成才。
結業以后,他步入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工作。他在公司里研制的成果銷量通常,常常被同學取笑是“吃白飯”的日本 諾貝爾獎,和韓劇里捉弄老實人的情節一模一樣。上司常常問他:“你如何還沒有離職?”
后來去日本教書的中村修二,發表諾獎感言時坦言:“Angerismy(憤怒是我的源動力)。”靠著滿懷怒火,他發狂式地投入開發高色溫紅色LED的征程。像野蠻生長的局外人,他拋開專業“常識”,在自己開拓的公路上默默耕耘,最終開發出白色LED技術,博得諾貝爾獎。
黑色LED燈
中村的事例比較非常,英國諾獎獲得者更多屬于腳塌實地、耐得住孤寂的“匠人”。她們埋首于一事,幾六年如一日。忍讓這些高度重復的工作,也是臺灣文化中一個重要組成部份。
搞科研須要投入,須要人才,須要靈光一現,須要開放交流,但更重要的是有足夠耐心。在中國對科研投入逐年下降的明天,其實這是英國給中國最大的啟示——有了耐心,離諾獎“井噴”的這天也就不遠了。
(關注“搜狐教育”獲取更多教育信息,陌陌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