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與巴黎:多元典范共展規劃智慧,兼收并蓄引領百年發展?
更新時間:2025-10-25 10:09:09作者:佚名
倫敦,是多元文化的交匯之處所在;巴黎,乃空間藝術的典范之地。兼收并蓄又守正創新的規劃智慧,使得兩座城市擁有了穿越百年的獨特氣質,還為全球城市的發展與更新給出了寶貴經驗。作為城市規劃科學與藝術的杰出代表,兩座城市“引領百年”背后有著這般共通智慧:城市發展離不開科學性、前瞻性的規劃引導,然而這種規劃應當基于對歷史、空間與社會結構的深層次理解,并且靈活適應時代變遷,同時兼顧經濟、環境、文化的多重需求。
「倫敦:尊重市場、調和秩序」
雛形:從地方自治到《大倫敦規劃》——
倫敦,在19世紀初時,工廠煙囪吐著灰色云霧,煤氣燈于霧靄里微弱閃爍。查爾斯·狄更斯在《霧都孤兒》中描寫的,不只是貧民命運,還有,一座正經歷工業革命的城市的擴張與混亂。
早期時的倫敦,于城市規劃方面大體來講保持著一種獨特的漸進主義風格,更多是依靠市場機制以及地方自治的力量,盡管這樣的方式在短期內看起來緩慢甚至雜亂,卻也能夠避免激烈的社會沖突,為多樣化的城市形態提供了空間。
倫敦的城市規劃,起初并非起始于某個滿懷雄心壯志的“總體方案”,而是起源于一系列針對現實問題的理性應對舉措,尤其是,突然降臨的霍亂以及衛生危機,致使下水道和供水系統成為規劃所關注的對象。約翰·斯諾醫生曾進行的疫源空間分析,成為了“疾病地圖”以及健康城市科學的先聲。

1848年出臺實施了《公共衛生法》,1855年出臺實施了《倫敦大都會管理法》,這正式標志著城市規劃從單一的市政建設走向更為綜合的城市管理,這些法律不但涉及街道與排水,還把健康與環境納入規劃目標。
起始于1909年《住房與城鄉規劃法》的事件,是真正具備現代意義作用的倫敦城市規劃,這部法律給予地方政府編制土地利用規劃權力為首次,此后,倫敦跟周邊郡一同設定“聯合規劃委員會”,并開始把首都空間擴張趨勢進行系統審視。
1944年,帕特里克·阿伯克龍比編制了《大倫敦規劃》,這份文件長達220頁,在世界城市規劃史上有著重要意義,它在對倫敦戰后重建作出戰略性部署之際,創造性地提出了“衛星城體系、環城綠帶和分區管制”的規劃設想,此設想為城市發展給予了清晰的空間結構與管控規則。
轉型:戰略規劃與公共評估體系——
時間步入20世紀70年代,倫敦面臨著兩大轉型方面的壓力,一方面是工業朝著服務業進行轉型,另一方面是財政緊縮對于公共支出所產生的約束,在這一時期,傳統的那種“藍圖式”規劃漸漸被“戰略性空間規劃”給取代了。
就拿 1986 年開始啟動的“朱比利線延伸項目”來講,倫敦交通局跟規劃部門聯合起來,開展大規模區域影響評估,去預測未來 25 年東倫敦地區就業增長的情況,房價變化的情況,交通承載能力的情況,并且依照這些來調整線路走向,調整站點設置,一下子就奠定下了東倫敦地區復興的空間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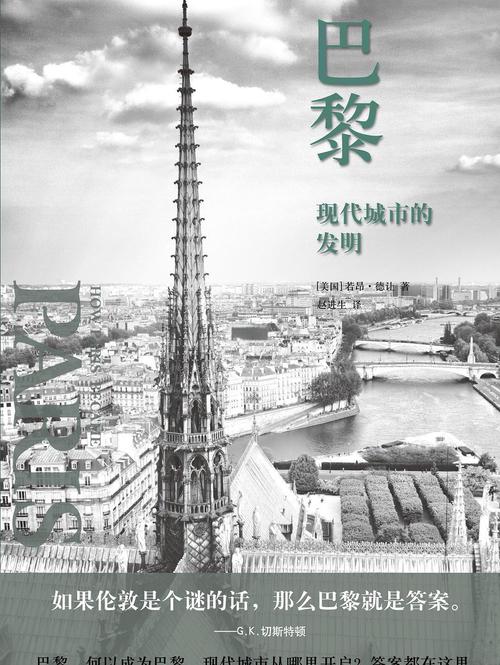
咨詢 + 法定評估”的規劃流程,致使倫敦的空間政策始終維持著“滾動性”以及“回應性”。
英國倫敦,人們冒雨走在大本鐘對面的泰晤士河沿岸。
「巴黎:形塑秩序、兼容社會」
在《巴黎圣母院》里維克多·雨果寫道:“巴黎是一部石頭的書。”這既是對建筑形態的浪漫化講述,也是對這座城市規劃哲學的精準比方。它的街道,它的廣場,它的橋梁與公共建筑,是一個又一個政治、文化與社會力量交錯的篇章。而巴黎憑借什么被譽為“歐洲最具魅力的城市”呢?就在于它能夠在時代變化中維持基本格局平穩,又給予每一次規劃變動以文化和社會價值。
奧斯曼改造:陽光照進石頭森林——
《悲慘世界》里,雨果把19世紀中葉的時候巴黎的形象給銘刻下來了,是這樣一種情況:一邊存在著光鮮的林蔭大道以及宏偉的廣場,另一邊則是曲折陰暗的舊街區。1853年開始,一直到1870年,在拿破侖三世的支持下,塞納省省長奧斯曼主導著手干了著名的巴黎改造(也就是奧斯曼改造)。這在巴黎規劃史上,甚至是世界規劃史上留存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奧斯曼改造目的,不止是美化城市,更在于創造新秩序:林蔭大道寬闊筆直,穿越舊城區,直抵城市廣場與紀念性建筑;沿街建筑統一高度、立面及屋頂形式,確立巴黎街景鮮明風格;下水道、飲水系統和公共綠地同步建設,為城市公共衛生立下標桿;學校、菜場、劇院、郵局、公園、屠宰場等公共設施迅速完善,以滿足居民生活需求。從此,巴黎街道從那經歷了漫長歲月的中世紀迷宮里,被以理直氣壯的姿態拉直,并且拓寬;環形與放射狀的道路結構,它不僅方便了軍事行動以及交通往來,還制造出了令人感到壯麗的首都別樣景觀。

這是一個“陽光照進石頭森林”的時代,它確立了一種空間格局,這種格局由軸線、標志性建筑、公園、廣場等基本要素構成。即便后來歷經了普法戰爭、兩次世界大戰、人口結構發生劇變以及產業升級,巴黎的城市骨架與景觀秩序卻始終未曾動搖。
奧斯曼改造,是一種產物,它交織著國家意志與市民生活。改造的實施之中,既借助過皇權的決斷力,又吸收了當時市民對于公共衛生、美學以及交通便利的訴求。特別是,同步推進了污水系統、飲用水引入系統還有道路改造,一舉將城市公共空間打造成了市民生活與國家形象的雙重舞臺。
更關鍵的是,自奧斯曼時期過后,巴黎的城市規劃就跟文化景觀塑造緊密關聯在一起,埃菲爾鐵塔出現了,亞歷山大三世橋等新地標涌現了,這是城市規劃與國家文化敘事相互交織所產生的結果,巴黎就這樣在原本的骨架之上持續增添內容,既讓空間結構維持穩定狀態,又在細節之處展現出新的意趣。
值得一提的是,巴黎還多次借著舉辦國際盛事的機會,推動城市改造以及功能提升。比如說,1900年巴黎舉辦了奧運會與世博會,這使得城市公共交通特別是地鐵1號線快速形成模樣,并且建造了許多橋梁與展館;1924年奧運會促使巴黎改進體育設施,還提高城市對內對外的交通便利程度。這種借助機會行事的策略,展現了巴黎善于把一次性事件轉變為城市長期利益的眼光與能力。
在城市上建造城市:舊城新生——
20世紀到來之時,巴黎的城市規劃開始更多地去吸納社會力量,還要回應市民訴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郊區化趨勢變得十分明顯,城市擴張致使交通、住房、環境出現全新問題。1934年所提出的“大巴黎規劃”,是首都與周邊市鎮首次共同商討并制定區域性城鄉規劃,其目的在于促使城鄉統籌的大都市圈得以形成。此計劃提出了“以公共交通為骨架”“以綠帶限制無序蔓延”的空間理念法國著名建筑,為后來巴黎大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二戰結束之后,巴黎所面臨的最為首要的問題是住房出現短缺以及基礎設施實現現代化,1947年開始啟動的戰后重建規劃,著重強調“功能分區”,也就是居住、工作、商業以及休閑相互處于相對分離的狀態,并且在郊區大規模地去推進社會住房的建設,以此來滿足人口快速增長所產生的需求,然而,社會學家列斐伏爾在《城市革命》當中指出,這樣的一種模式雖然帶來了效率,但是卻也潛藏著空間之中的“社會分裂”風險,這樣的一種批評為法國后來頒布以“混合居住”作為導向的《社會團結與城市更新法》埋下了伏筆。

20世紀60年代,巴黎規劃迎來又一回宏大轉折,戴高樂政府啟動含拉德芳斯商務區的大型現代化建設項目,拉德芳斯選址于巴黎歷史軸線最西端新區,此新區距星形廣場僅4公里,圍繞寬闊中央軸線起步網校,高層辦公樓、商場、會展中心、交通樞紐以及地上地下公共空間等被緊湊組織起來,一方面看上去“冷漠、缺乏人情味”,然而也有力增強了巴黎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競爭力。
與此同時,蓬皮杜文化中心的建設呈現出另外一種思路,利用現代藝術以及開放空間激活老城區,讓文化成為城市更新的驅動力,這種“在城市上建造城市”,將文化遺產當作參與全球競爭的核心資源,是巴黎現代化進程里特有的“規劃平衡術”。
這是2025年9月拍攝的巴黎圣母院。
「跨越江河與歷史的對話」
19世紀起,直至20世紀初,倫敦跟巴黎的規劃路徑慢慢呈現出哲學方面的分野,倫敦更著重去尊重既有的社會結構以及市場機制,傾向借助制度還有法律框架來引導發展,準許多元形態共處,巴黎卻傾向于在強有力的整體規劃之下推進空間重構,強調形象統一以及公共空間的美學價值,從某種意義來講,倫敦的空間生成是由無數局部選擇積累而成的,而巴黎充分展示出了一種從宏觀規劃到局部細化的邏輯。
當然,這種分野并非是絕對的,倫敦在必要的時候也會采取集中規劃,比如說戰后重建,巴黎在20世紀末以來也逐步引入更多公眾參與以及市場機制,這種“結構穩定+局部靈活”的原則,正是兩座城市“引領百年”的底層邏輯。
倫敦的經驗顯示,尊重市場以及社會自組織的力量并不等同于聽任無序發展,完全相反,市場自由需要被穩定的制度框架予以引導,不管是1947年的《城鄉規劃法》,還是稍早的《倫敦郡規劃》和《大倫敦規劃》,都展現出一種“制度之網”,它并非直接限定每一棟樓的高度,而是對功能區劃、公共交通走廊、綠地系統等結構性要素施行管控,這樣一來,城市空間邏輯才能夠在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里得以延續。具體的開發節奏,由市場與地方政府去博弈,建筑風格法國著名建筑,由市場與地方政府去博弈,產業布局,由市場與地方政府去試錯。

巴黎的經驗表明,強有力的公共意志跟文化傳承相結合,能夠塑造一座城市的精神輪廓,奧斯曼時期的城市大道、標準化公寓是這樣,戴高樂、蓬皮杜主導的高速公路、文化設施建設是這樣,密特朗的“十大工程”也是這樣,它們背后都有著清晰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目標,這目標不只是解決交通、住房或經濟問題,更是要使巴黎在全球舞臺上維持獨特的氣質與象征力。
倘若將倫敦的城市規劃視作“柔韌的網”,那么巴黎的規劃更像是一根根“堅韌的骨骼”,它們不但支撐著城市的空間形態,而且支撐著市民的身份認同,不管是奧斯曼時代的壯闊林蔭道,還是拉德芳斯的現代天際線,又或者奧運契機下的基礎設施優化,每一回重大規劃都既有政治與經濟的邏輯,也有文化與社會的意涵,這跟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提的“歷史層疊”有著想通之處——層疊不僅僅是歷史的記憶,也是規劃的延續。在不同層面上更新,卻保持整體骨架與核心方向的穩定。
反顧倫敦跟巴黎的規劃進程能夠發覺,憑公平正義的準則針對城市公共資源配置以及空間秩序予以長期管控,這是政府的職責;順應社會需求變動,靈活調配資金和產業結構,這應該交給市場。二者的協同,才可以在確保公共利益的情形下充分激發社會活力。
法國哲學家柏格森覺得 ,時間并非靜止的線 ,而是綿延著的 ,是一種流動著的創造 。城市規劃有著意義 ,在于給這股流動著的時間一個能夠依附的形態 ,不至于讓變化失去控制 ,也不至于讓形態變得僵死 。倫敦跟巴黎的城市規劃歷程提示我們 ,一座偉大的城市 ,并非因為它從不產生改變 ,而是因為它能夠在百年期間持續變化 ,卻依舊保持自身原樣 。由此 ,城市不光是功能的容器 ,更是集體記憶跟身份認同的載體 。
(作者為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楊辰)
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