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范大學轉型之路:堅守師范教育本色,道器兼修育英才
更新時間:2025-11-13 20:19:26作者:佚名
師范大學朝著綜合大學進行轉型,這并不等同于“轉身”,師范教育屬于師范大學具備的優勢特色,它同時也是一種責任擔當,對于師范教育而言,只能夠予以加強,絕對不可以進行削弱。
于資源競爭越發激烈之處,大學排行榜紛紛涌現,各種「名號」極具吸引力之際,同行之路寬廣,光榮使命需共同「分享」。

百年來,我國師范教育體系歷經了這么一種變遷,最開始是由相對而言獨立的師范教育機構單獨承擔,后來變成多種類型機構廣泛參與。師范院校在此期間也產生了變化,從行業性機構朝著綜合性大學進行轉型。在這個組織范式轉化旅程中,全國各個師范大學一同面臨“師范教育向何處去”這一課題。而要回答師范教育究竟走向何方,首先得針對教師職業展開理性思考。
教師職業需要“道”“器”兼修

在當下,不存在任何一種職業,會像教師這般,并被全社會予以關注、評價以及議論,這里面既有不少贊美,然而更多的卻是非議,文化傳統以及社會制度針對教師職業所構建起來的“紅燭”“春蠶”的那種“圣神化”形象,已然在不同程度方面遭受侵蝕,教師群體于不同程度上承受著信任危機,一方面,好像教師集體卸掉了“道德重負”,進而回歸到“常人”生活,教師職業逐漸蛻變成了“飯碗職業”留學之路,另一方面,教師的培養愈發偏重精致技術,從而走上了所謂“真正的專業化”道路 。師德教育的標準與要求,相比專業技能超越常人,找不到有效的養成路徑,所以似乎難有作為。其可能的后果是,聚焦學生學業成績的教學能力和教學技能受重視,重實踐應用、重技術操作、重績效表現成教師培養新價值訴求,傳統的“傳道、授業、解惑”三大任務受擠兌,“器彰而道隱”。塑造“人格”、“精神”和“靈魂”等形而上的理想追求被奚落為“不接地氣”的大詞。好似,網絡潮語,像“萌嗒嗒”“哥只是個傳說”這般,引發掌聲的那種討巧,才回歸質樸真切。
認識以及評價教師職業,不能從一種極端走向另一種極端,事實上,教師職業以往從來不是一般職業能夠相比的,揚雄早在漢代就界定說“師者,人之模范也” ,司馬光“經師易得,人師難求”的感慨也是意味深長的,陶行知先生“學高為師,身正為范”更是高度概括了。北京師范大學的校訓呢,是“學為人師,行為世范” ;華東師范大學的校訓當中有“為人師表” ;東北師范大學的校訓里同樣有“為人師表” ;臺島師范大學校歌存在“師范尤尊崇,勤吾學,進吾德,建吾躬”的詞句 ;高雄師范大學校歌也包含“師資孕育,師道尊崇,進德修業,學貫西中”的歌詞。像這樣的情況還有很多。在我們這些被稱作“師范大學”的學校,從校訓、校歌方面來看,沒有不重視“德表”的。應當講,這樣的執著堅守永遠都不會過時。于專業化敘事的大背景當中,教師所承擔的道德責任并非是減縮了,反而是要求變得更高了。“道”與“器”兼修這是教師職業的內在訴求。唯有將道德意蘊跟專業素養相互結合起來,才會有教師職業的崇高以及尊嚴。北京師范大學設立了啟功教師獎,對在鄉村工作30年以上的教師予以重獎。他們的學歷不一定有多么高,然而他們擁有一顆愛心,他們擁有執著與堅守,這恰恰是教師職業的靈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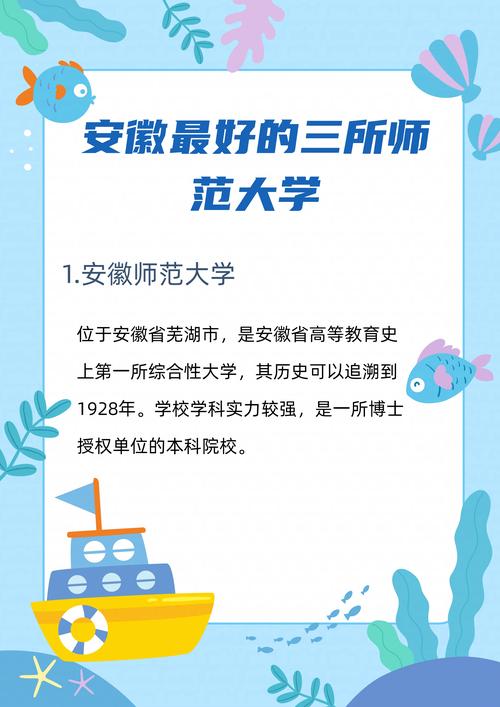
師范大學發展需要“轉型”而非“轉身”
從1897年所成立的南陽公學師范院開始,到1902年成立的南通通州師范學堂,再到同一年成立的京師大學堂師范館,從1902年《欽定學堂章程》對應的“壬寅學制”,到1904年《奏定學堂章程》對應的“癸卯學制”,以及1907年的《女子師范學堂章程》,還有1912年至1913年《壬子癸丑學制》里的《師范教育令》,晚清以及民國初期我國師范教育系統逐漸建立起來,形成自成一統的局面。盡管曾受到1922年“壬戌學制”的影響,然而最終確立了自主的師范教育系統。新中國成立初期,構建起涵蓋初級師范、中等師范、師范專科以及師范大學的所謂四級師范體系,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摒棄初級師范,進而形成了三級師范體系,“文革”結束之后,師范教育系統的運行得以恢復,自20世紀90年代往后,逐漸開始在層次與機構方面做出某種調整,施行從“三級”邁向“二級”乃至“一級”這樣的師范教育體系轉移進程,逐漸雕琢出以師范院校作為主體,并且有著其他高等學校參與其中的開放性教師教育體系。在這個進程里面華東師范大學校訓,中師不見蹤跡了,師范學校更改名稱并且提升等級,師范大學陸陸續續踏上朝著綜合大學轉變的路途。曾經有一陣子存在著“學術性”與“師范性”這樣的爭議情況,變成了高師院校身份認定方面的關鍵要點。當“教學型”以及“研究型”成為新的劃分標志之際,很多高師院校開始在研究型與教學型之間進行排列組合,確定站隊的位置。經由高等教育體制改革“調整、合并、合作、共建”這一八字方針的帶動指引,巨型綜合性大學突顯出來,而沒有進行合并的行業性大學開始朝著綜合性大學轉變。師范大學也參與到其中了。師范大學朝著綜合性大學轉變之后,師范教育要如何處理呢?大學里面的教師教育學院與其他專業性學院處于同等地位之后,怎樣去堅守傳統師范教育所具有的“師道”價值呢?又該如何堅守“師德”價值呢?以及如何堅守“師表”價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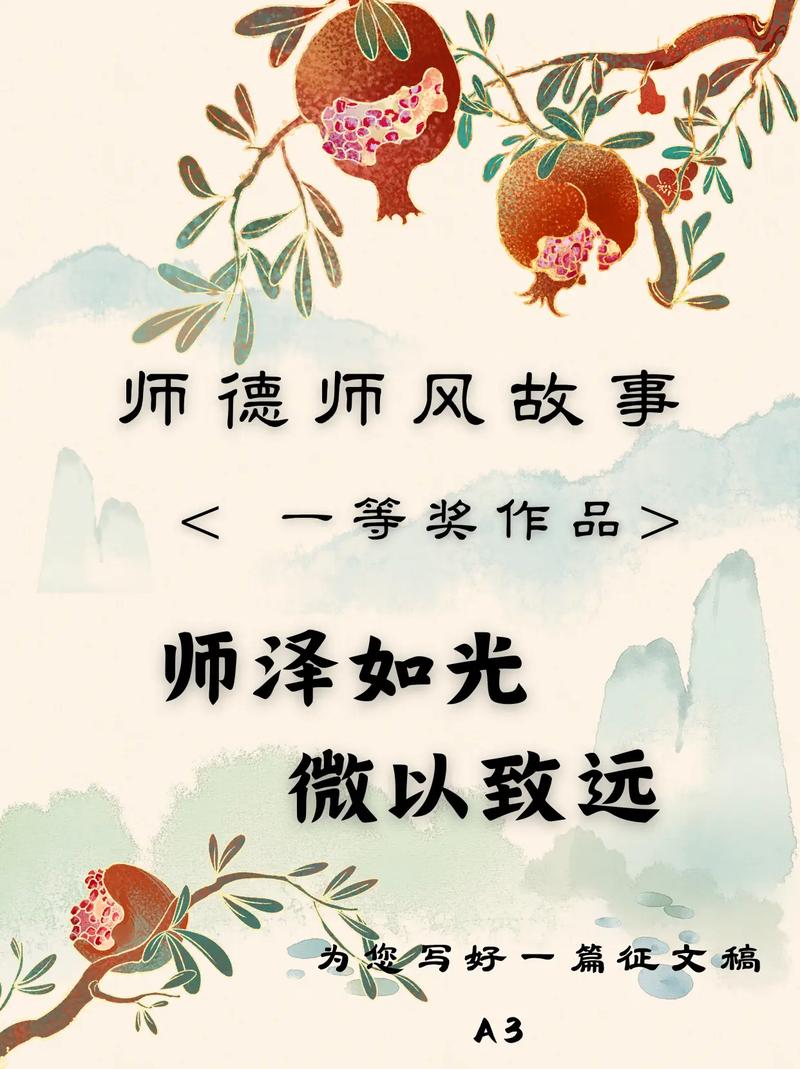
師范大學開展加強科學研究之舉,同時朝著綜合大學方向進行轉型,這是針對社會所需做出的積極回應,亦是大學自身謀求發展的明智抉擇。然而轉型并非等同于“轉身”。不管是從組織戰略層面予以考量,還是按照國家使命來審視,師范教育既是師范大學的優勢特色所在之處,同樣也是其應盡責任擔當所在之處,只能夠予以加強,絕對不可以進行削弱。一味守舊、因循守舊是行不通的,盲目求新、包攬一切同樣會產生問題。師范大學朝著綜合化方向轉型,是在充分發揮學科優勢,凸顯師范特色的前提條件下,做到有所行動有所不為的綜合化,并非是為了綜合化的名聲而去搞綜合化。南京師范大學于2005年在設有教育科學學院之際成立教師教育學院,用以探索“大學+師范”模式。北京師范大學組建教育學部時,創立了具備統籌全校師范教育資源職能的教師教育學院。鑒于學科教學論的教師分散于不同學院,所以把它定性為跟教育學部相聯系的“綜合交叉教學平臺”。華東師范大學在成立教育學部之后,又設立教師教育學院,這同樣是針對綜合化進程里怎樣保持優勢特色、“面向師范”的一番努力。在校這一些地方的機構究竟該怎么去進行協調,體制以及一套機制到底得怎樣去確保師范教育所具備的品質,教育的整個過程又要怎樣去促使“道器兼修”,這些都是需要持續去加以關注的。
師范大學共同體建設要“分享使命”而非“華山論劍”
教師,是對未來有著巨大影響的特殊群體,師范教育,是觸摸未來的事業,《學記》講,“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學”,一個民族,若有足夠多優秀教師,便會成為最具希望的民族,一個道尊、敬學的社會,是教師教育最大的發展動力,在與時俱進、綜合發展之際堅守師范特色,就是堅守所有師范大學的共同信念與價值,培養德才雙馨、道器兼修的優秀教師,乃是師范大學的共同利益,亦是共同使命。

師范教育屬于高等教育里重要的構成部分,師范大學面臨好多共同的問題以及挑戰,有著諸多共同的課題與期盼,在資源競爭越發激烈,大學排行榜還有各種“名號”吸引目光之際,各個學校難免會去制定策略,找出路徑,突出重圍,越是處于這樣的時候,就越是得思考一下,從更大的時空范圍來思量,從使命擔當的層面去觀察,師范院校到底是算一還是算多呢的,大學發展的目標是那種誰勝誰負、華山論劍的名次之爭華東師范大學校訓,還是去激發、錘煉以及運用我們的力量來教化當下,滋潤未來呢的 ?用不著多說,答案自明。同行之路寬廣,光榮使命需一同去“分享”。(作者周作宇,其為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還是教授,也是博士生導師)。
《中國教育報》2015年12月16日第4版